建立科技伦理,让科技为人而不是伤人,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

01
近读张宏良教授《令人兴奋的中国科技知识分子和令人忧虑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》一文,深以为然。并产生了为张教授的深思远虑,作一些呼应性工作的冲动,于是,便有了这篇文章。
张教授说的没错。当下中国的科技知识分子很牛帮,当下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很拉垮。前者让中国科技大爆炸,后者“对于当今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所有伟大发明,不是研究如何运用这些发明让人类飞跃到更高发展阶段,如何建立能够保证现代科技,只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,而不是用于人类毁灭的科技伦理,而是欢呼用这些科技成果,能够从全世界赚取更多财富,欢呼这些科技成果,能够把其他国家的人类踩在脚下,甚至把其他国家的人类推向毁灭,今天要把日本变成一片焦土,明天要把美国变成一片焦土。”是的,这样下去将十分危险,因为,按这些人的“指引”,飞速发展的科技成果,只会导致人类的灭绝而“不是把人类送入大同世界”。
我们也跟张教授一样,感知到了建立与科技大爆炸相适应的科技伦理,已经迫在眉睫。能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,关乎生死。
02
解决科技发展遭遇的伦理滞后困局,是一场智慧世纪的文明挑战。在量子计算机突破“算力极限”的今天,在ChatGPT4.0和DeepSeek等AI展现出类人智能的此刻,在基因编辑技术即将叩开生命设计之门的当下,在全球AI专利申请量较十年前增长37倍,中国贡献了其中62%的增长的现实面前,在这种指数级的技术跃迁,使得培根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箴言、正在成为“技术就是权力”的演变、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的时候,我们却尴尬地发现,指导科技发展的伦理框架,仍然停留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思维范式。

“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不在于技术本身,而在于人类对技术本质的误解。”这是海德格的话,说得十分到位,也指出了科技伦理的极其重要。是的,马有千里之程,无骑不能自往。如果说科技是匹烈马,科技伦理就是马羁和缰绳。没有相应的科技伦理引领,高速发展的科技,将是人类的自掘坟墓。
中国科技的大发展形势喜人,形势逼人。我们已经在量子通信、可控核聚变、空间站建设、人工智能等领域,取得了突破性成就。既彰显出东方智慧的现代复兴,但也暴露出科技伦理建设的深层危机。当我们的“九章”量子计算机以200秒完成超级计算机6亿年的运算任务时,当“嫦娥六号”从月球背面带回珍贵样本时,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、应对这些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地震?非常遗憾,至今我们还不能作出肯定回答。
中国科协发布的《科技工作者伦理意识调查报告》显示,仅有37%的科研人员接受过系统的伦理培训,科技伦理委员会在企业的覆盖率不足15%。这种失衡正在制造新的文明危机。比如,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全球震荡,算法歧视导致的就业市场扭曲,AI深度伪造技术催生的信任危机等等,无不昭示着科技发展已经来到了伦理抉择的十字路口。

而且,当代知识分子中相当多的人,已经深陷精神困境。在深圳科技园的摩天大楼里,工程师通过调试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,可以精确计算出系统运行的每个参数,却无法回答“AI是否应该拥有情感权利”这样的基础伦理问题,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的认知割裂,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。
同时,科技知识分子沉浸在技术突破的狂欢,人文知识分子却在消费主义的浪潮里逐渐迷失。某知名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,76%的文科研究生将“财务自由”作为人生首要目标,仅有12%的学生关注社会伦理议题。这种精神矮化使得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哲学追求,在当今演变成了“知而不行”的犬儒主义。
更令人忧虑的是,部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正滑向危险的深渊。在某网络论坛,超过60%的参与者支持“为科技优势可以不择手段”的观点;某高校教授公开宣称“伦理是阻碍科技进步的绊脚石”。这种思潮,与16世纪马基雅维利主义复活形成诡异呼应,若不加以纠正,将会使整个社会体系崩溃。
事实告知我们,我们正在重蹈宋明时期“重术轻道”的覆辙。我们的耳边仿佛听到了、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那句不朽名言发出的警示:“器物之利,不若人心之正”,振聋发聩。
03
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敲响警钟。回望历史,纵观宋明两代的科技辉煌与伦理失序,我们能清晰看到技术发展与文明存续的辩证关系。
北宋时期,中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60%,钢铁年产量达到15万吨(相当于18世纪整个欧洲的产量),但程朱理学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伦理框架,始终未能将技术突破转化为制度创新。正如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指出的,当利玛窦带来《坤舆万国全图》时,明朝士大夫更关心的是“夷夏之辨”而非地理大发现。

这种伦理认知的错位,使得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积累的航海技术,最终沦为“片板不得下海”禁令的牺牲品。纵是有了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哲学突破,也始终未能与同期《天工开物》的技术成就形成思想共振,这种伦理与科技的断裂,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的屡屡错失机遇和落后挨打。
而同一时期的康德却提出了“人是目的而非手段”的全新观念,构建了现代伦理基石。20世纪约拿斯提出的“责任伦理”,又为科技时代指明方向。这些思想遗产构成科技伦理建设的四维坐标系,让人性维度守护人的尊严,让自然维度维系生态平衡,让社会维度保障公平正义,让代际维度延续文明火种。
与宋明同时期的还有佛罗伦萨,美第奇家族建立的人类首个科技伦理委员会。他们将古希腊哲学、基督教伦理与新兴科学技术有机结合,催生了达芬奇、伽利略等跨界天才。这种“技术-伦理”协同发展的模式,在瓦特改良蒸汽机时,便已形成了专利制度与劳动伦理的双重约束,在爱因斯坦提出质能方程时即有《罗素-爱因斯坦宣言》的伦理预警。
这种东西方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配套建设上的差异,最终使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载的活字印刷术,成了欧洲宗教改革的思想利器;明代万户的飞天(也是人类首次飞行试验)壮举,在西方演变为阿波罗登月。无庸置疑,这种科技发展与伦理建设失衡的历史教训,在今天愈发显得无比重要。

是的,我们近代之所以由领先西方沦为落后西方,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就是科技伦理约束了科技发展。西方之所以由落后我们到赶超我们,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让科技伦理为科技发展插上了翅膀。
需要指出的是,无论是我们的教训还是西方的经验,都已经过时。当代科技伦理,必须比以往的科技伦理更为先进,更为高级,才能达成“马的有骑千里之乘”。我们在这里回望历史,目的也是为了阐明科技伦理的重要,而不是旨在袭旧。
04
那么,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科技伦理呢?对此,国家正在着力展开这项重大工程建设。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,确立了科技伦理原则,明确了科技发展的价值导向。这就是:增进人类福祉、尊重生命权利、公平公正、风险控制、公开透明。

增进人类福祉,就是科技活动应以提升全人类生活质量、促进社会公平为根本目标,避免技术滥用导致社会分化或生态破坏。例如,基因编辑技术需严格限制于疾病治疗,而非“设计婴儿”。
尊重生命与人性尊严。主要是从设立禁区来体现。比如,禁止涉及人类生殖细胞编辑、脑机接口侵入性应用等可能颠覆生命本质的研究,确保技术应用不损害人格尊严等等。
公平公正与风险可控。即技术开发需避免算法歧视、数据垄断等问题,确保技术红利普惠共享;高风险领域(如人工智能、合成生物学)需建立清单化管理与动态评估机制。
公开透明与可问责。主要是科技活动应公开关键信息(如数据来源、算法逻辑),并建立责任追溯体系,明确技术开发者、应用方及监管者的伦理责任
一句话,就是要让科技发展为人类造福,坚决不让科技发展成为人类的灾星。
在我们看来,实现这一科技伦理建设的既定目标,建立与科技大爆炸相适应的科技伦理,既要求我们既要吸收儒家“仁者爱人”的道德智慧,又要融合道家“道法自然”的生态哲学,还要汲取佛教“众生平等”的慈悲精神。
一是用中华“天人合一”的传统智慧,破解当代科技伦理困境,构建融合“天人关系、人机关系、群己关系、代际关系”的四维框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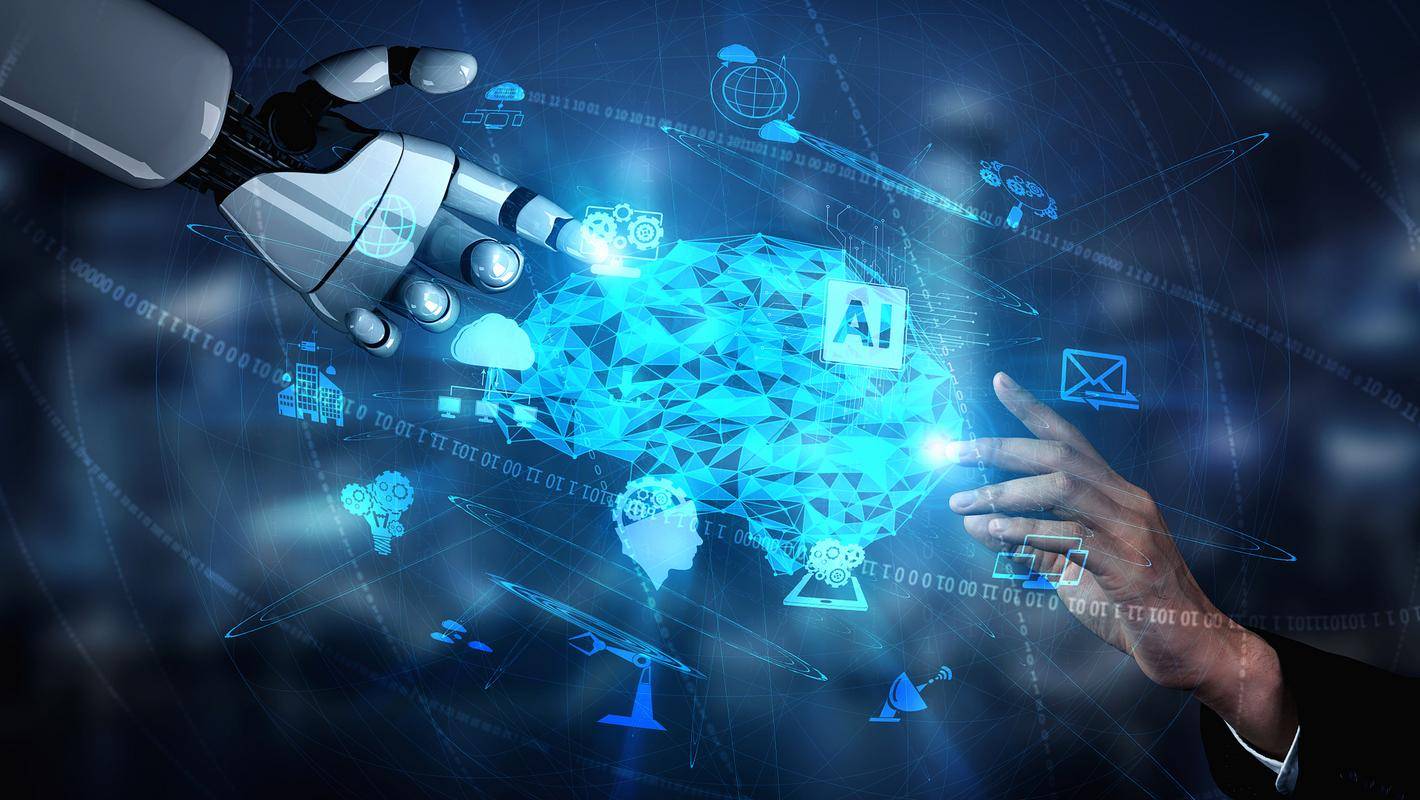
二是实现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生态智慧,以及“兼爱非攻”的和平利用理念的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,防患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伤害。
三是建立“理在气中”,“算法向善”的儒家式原则,强化“科技为民”的责任伦理,彰显中华伦理的当代价值。
四是激活“天下为公”的政治智慧,促成“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”的文明观念,让科技发展越过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。
五是以“万世开太平”的远见,让“民胞物与”思想,转化为可操作的代际正义框架,给科技发展注入“宇宙关怀”。
与此同时,我们更要立足现实,构建多层次治理体系,实现科技伦理的全链条监管,并强化科技伦理的动态治理与前瞻性研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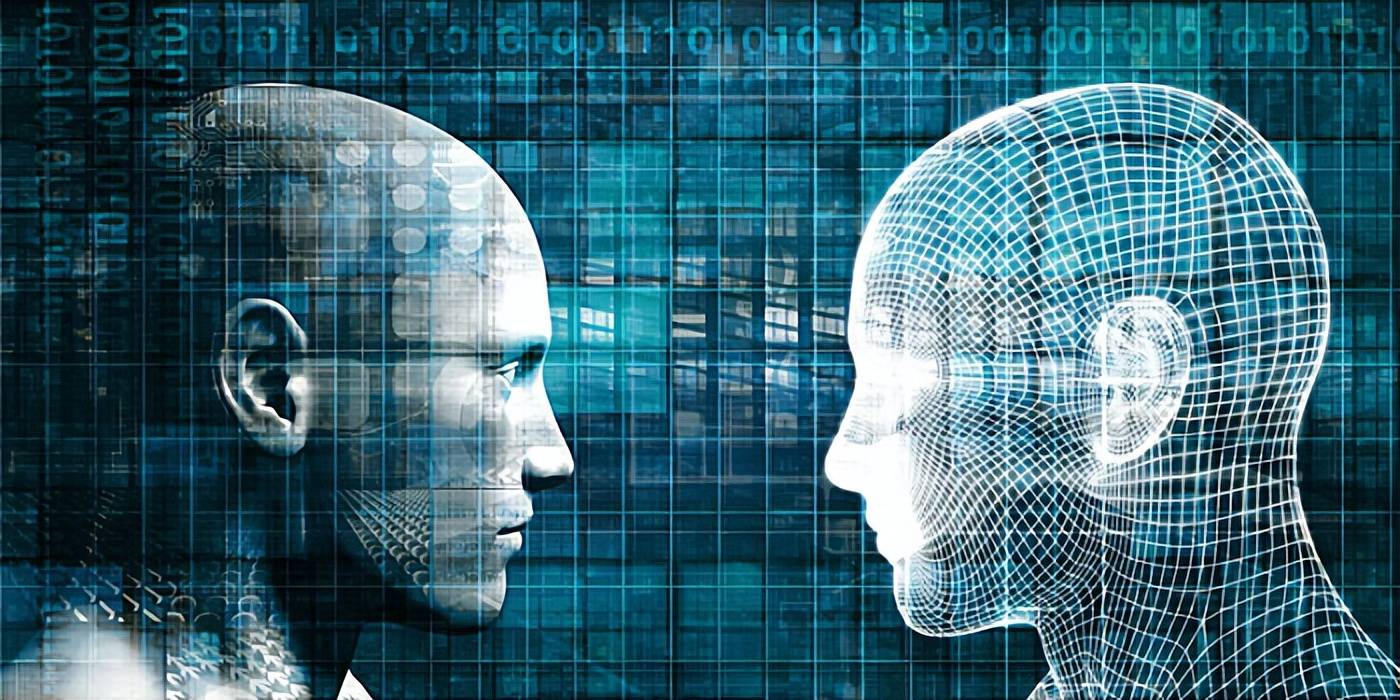
一是国家主导的顶层设计,要完善法律法规,推动生命科学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伦理立法,将伦理规范上升为法律约束。
二是要分级分类管理,制定“高风险科技活动清单”,对基因编辑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施严格审查与动态监管。
三是要多方协同共同治理。政府、企业、科研机构、公众共同参与,建立三级伦理审查体系:微观层面的企业伦理委员会,中观领域的行业伦理标准,宏观维度的国家伦理法规。将伦理审查嵌入研发流程和成果应用全过程。
四是跨学科合作。整合哲学、法学、社会学等学科资源,解决技术复杂性与伦理争议的交织问题。
五是聚焦中国社会特有的技术伦理挑战。如老龄化社会中的智能养老伦理、数字经济中的隐私保护等,避免照搬西方伦理框架。
六是坚持制度创新与文化自信。通过政策引导将伦理原则转化为行业标准(如大模型伦理审查指南),并培养兼具科技素养与伦理意识的专业人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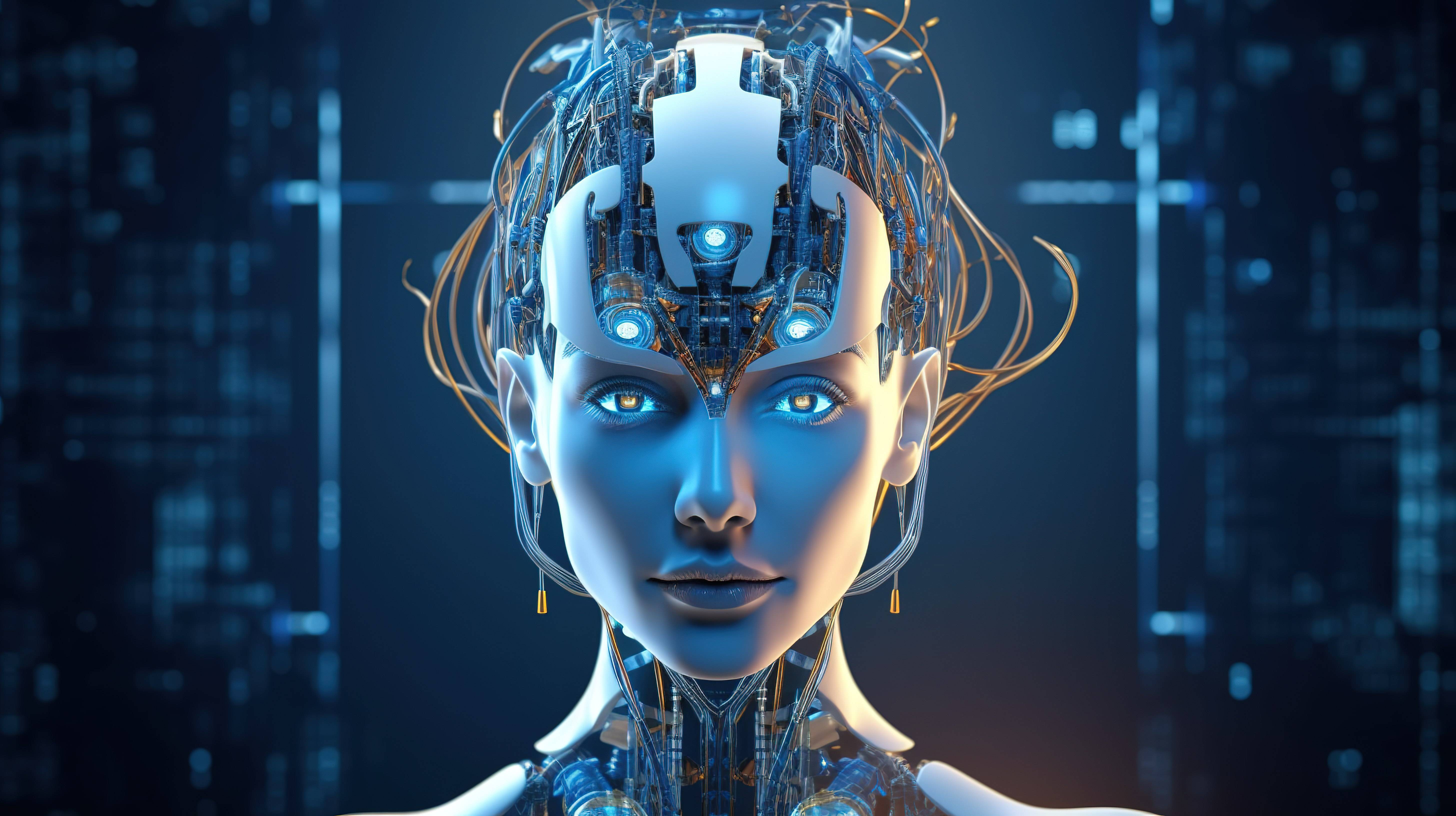
七是强化敏捷治理与伦理先行。如对新兴技术(如量子计算、元宇宙)建立“适应性治理”模式,通过沙盒试验、伦理预评估提前识别风险等等。
八是展开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伦理教育与公众参与。将科技伦理纳入高等教育体系,培养应用伦理专业人才,通过公众听证、技术透明化增强社会监督等。
九是响应全球协作与责任共担。积极参与国际科技伦理规则制定(如全球AI伦理公约),推动技术标准的跨国互认与风险共治等。
十是强化监管,层层落实责任制。一旦发现伦理失守事件,一定追责到底。该罚的罚,该判的判,该杀的杀,决不手软。
如此等等,通过法律与制度划定底线,以文化自觉和创新思维,引导技术服务于人类共同价值,体现科技伦理向善的本质,并让科技这匹烈马,始终奔跑在“科技向善”造福人类的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。
05
特别需要强调的是,能不能建立现代科技伦理,人文知识分子责无旁贷,必须完成从“旁观者”到“共建者”的角色转变。道理也不难懂,因为,这本身就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分内事。如果这件事都干不成,那就不配人文知识分子这一称号,就应该被淘汰也必然被淘汰。
需要强调的是,人文知识分子能不能肩负起建立当代科技伦理这一历史时代使命,关乎国家与民族的生死。
我们认为,人文知识分子要肩负起建立当代科技伦理的历史时代使命,特别需要在如下两方面下真功夫,苦功夫,大功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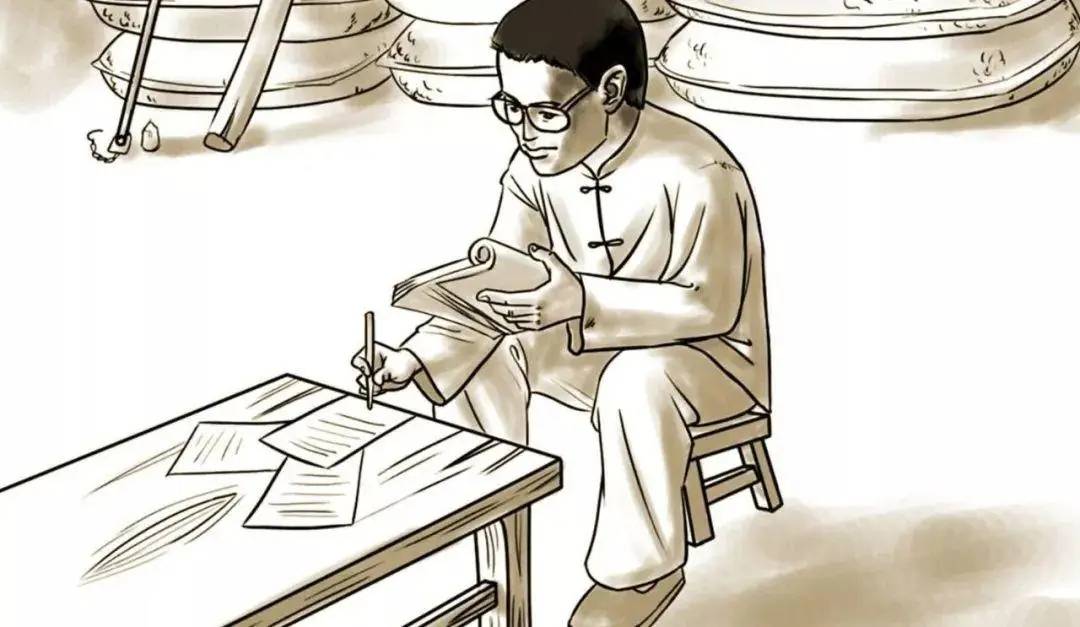
一是在能力上,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实现三种能力的跨越式提升。首先是传统伦理的现代化阐释能力。如将“物致知”转化为负责任创新原则。其次是科技前沿的伦理预判能力,类似朱熹“即物穷理”的功夫在脑机接口领域的应用。再次是全球治理的规则创设能力,重现郑和下西洋时的文明对话智慧。
二是在实践路径上,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建立“三维联动”机制。在理论层构建“新经学”阐释体系。比如,将《周易》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”的智慧,转化为科技伦理认识论;在制度层需要完善“伦理影响评估”体系,建立诸如《周礼》六官制衡思想式的多方治理架构;在文化层需要塑造“科技向善”的集体认知,通过“数字敦煌”等文化科技融合项目,重现《考工记》“天有时,地有气,材有美,工有巧”的造物伦理。
需要强调的是,中国提出的“人类命运共同体"理念,为科技伦理建设提供了哲学指引。就像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而非枪炮,能不能成为科技伦理的国际准则,同样需要人文知识分子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当然,建立当代科技伦理,科技知识分子也不能置身事外,也无法置身事外。都应该为此积极工作,至少也应该保证自己的科研工作,贯穿科技伦理,不踩红线不犯规,就像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带去的是瓷器而非枪炮一样,自觉肩负起“己欲立而立人”的伦理品格。
科技发展永远需要伦理导航。这不仅是防止“技术异化”的防火墙,更是文明跃升的推进器。
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,就是要做科技时代的“司南”,以“为天地立心”的胸襟,“为生民立命”的担当,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传承,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远见,构建起与科技革命相适应的伦理体系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避免重蹈“四大发明西传”的文明遗憾,避免科技爆炸伤害我们自己和人类,真正实现科技大国和文明强国的双重历史性跨越,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,这是文明延续的必然要求。让我们以张载“民胞物与”的胸怀,以张衡“效象度形”的求真精神,以王阳明“致良知”的勇气,以伟大的“长征精神”“抗战精神”、“两弹一星精神”、“抗洪抢险精神”,共同书写科技时代的伦理篇章,在科技爆炸的时代重建伦理秩序,为我们自己,为人类文明点亮理性的航灯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