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典庄园戏韵浓:戏曲声里暗藏人间百态与时代何种回响?
️【产学研王教授视点】暮春的午后,阳光斜斜洒在青砖灰瓦的飞檐上,斑驳的树影在回廊间摇曳。这座始建于清朝的江南园林式庄园,曾是当地望族的府邸,如今虽褪去了昔日的金碧辉煌,却因一曲《牡丹亭》的婉转唱腔,重新焕发出别样的生机。戏曲声里,小姐、公子、丫鬟与老者的故事徐徐展开,将古典庄园的时空褶皱层层揭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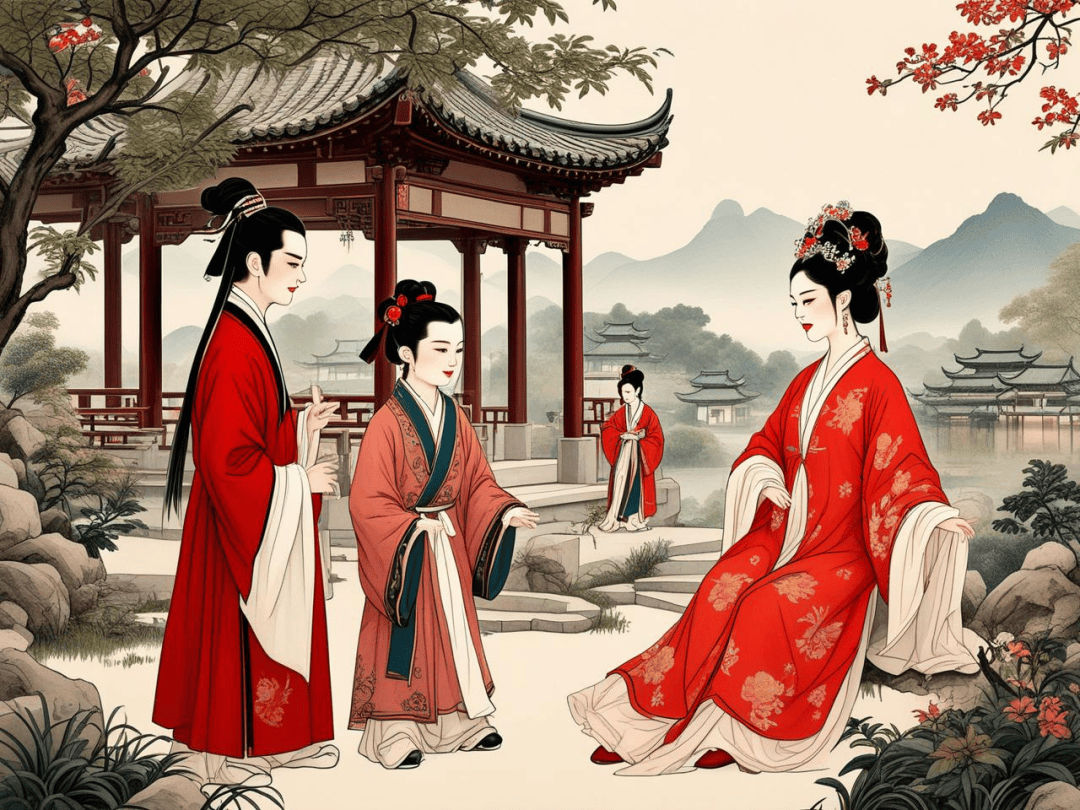
️一、戏曲声起:庭院深深锁清秋
庄园东南角的戏台是整座建筑群的灵魂所在。这座由楠木搭建的八角亭台,檐角悬着铜铃,风过时便与台下的流水声交织成韵。此刻,身着月白襦裙的柳家小姐正倚着雕花栏杆,指尖轻叩栏杆上的莲花浮雕。她的目光穿过满园芍药,落在正在排练《牡丹亭》的戏班身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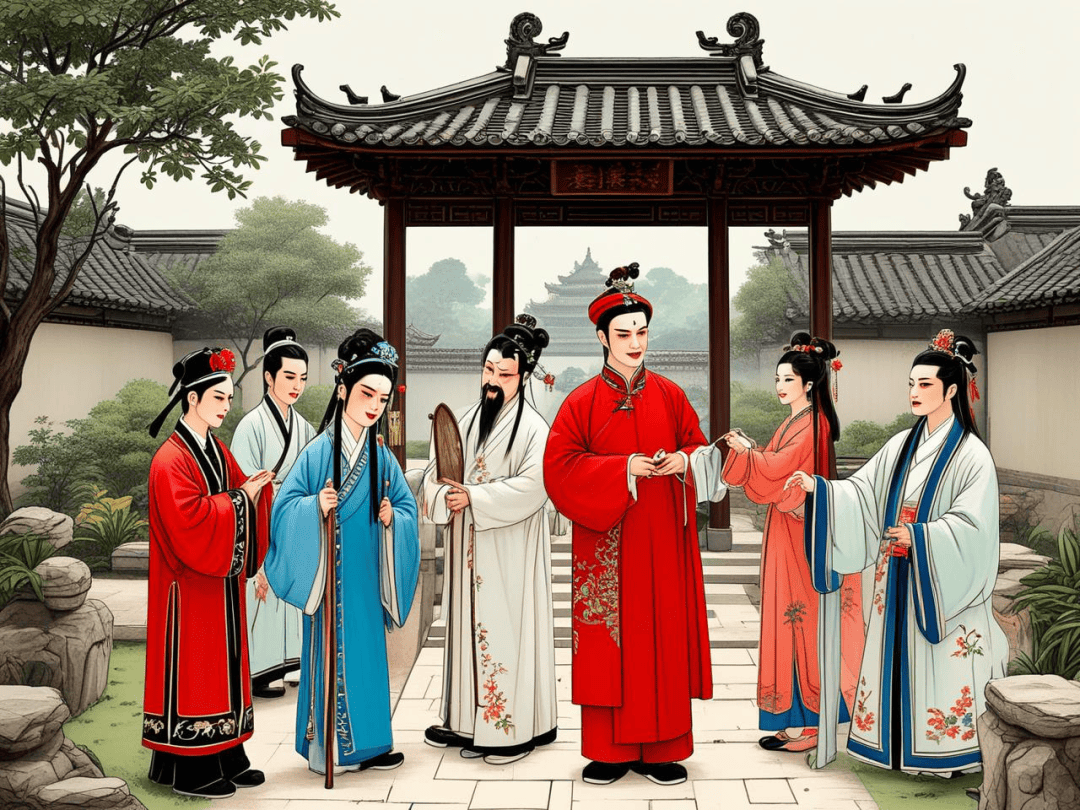
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”杜丽娘的唱腔如泣如诉,扮演者是柳家从苏州请来的名角儿苏婉娘。这位年方二八的旦角儿,眉眼间竟与柳小姐有七分相似——都是柳叶眉下藏着三分愁绪,朱唇轻启时带七分灵动。丫鬟小桃捧着青瓷茶盏凑近:“小姐,这出戏您都听了二十遍了,怎的还这般入神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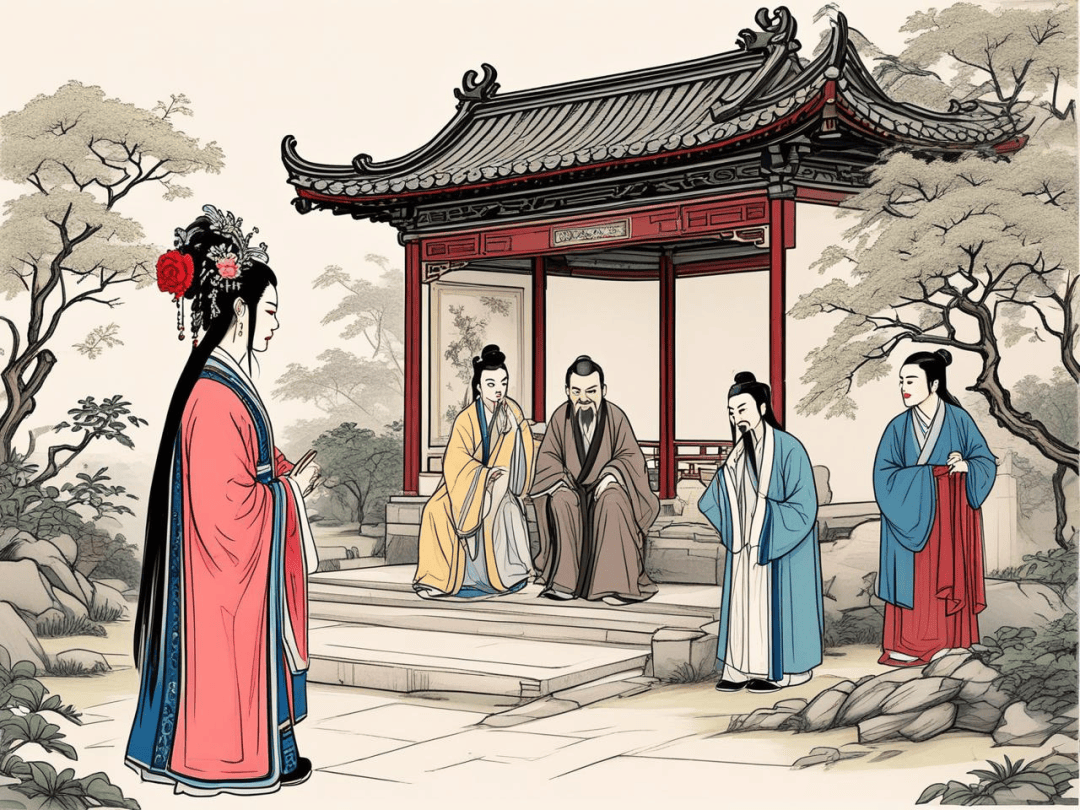
柳小姐接过茶盏,指尖摩挲着盏壁的缠枝莲纹:“你且看那杜丽娘游园惊梦,何尝不是我的写照?”她目光转向远处回廊下与账房先生对账的兄长。这位柳家独子自幼随父经商,如今已能独当一面,却总念叨着要将庄园改建成纺织工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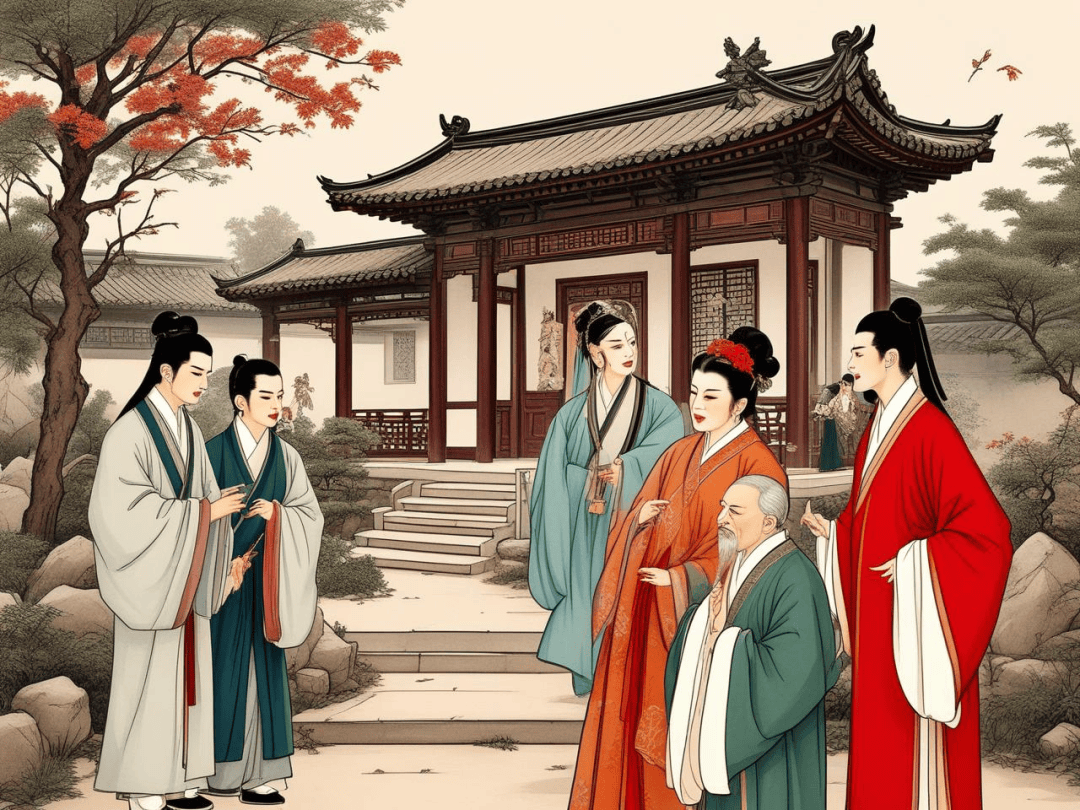
戏台西侧的月洞门后,老管家陈伯拄着紫檀拐杖,正与花匠老周低声商议:“这牡丹亭的柱础该修了,前日里小姐踩着青苔险些滑倒……”话音未落,忽听得戏台传来“咣当”一声——原是饰演柳梦梅的小生不慎碰翻了道具书案。苏婉娘连忙扶起对方,两人相视一笑的瞬间,陈伯浑浊的眼眸忽然泛起涟漪,仿佛看见五十年前,自己给老爷抬轿时,轿中那位与戏子私奔的二小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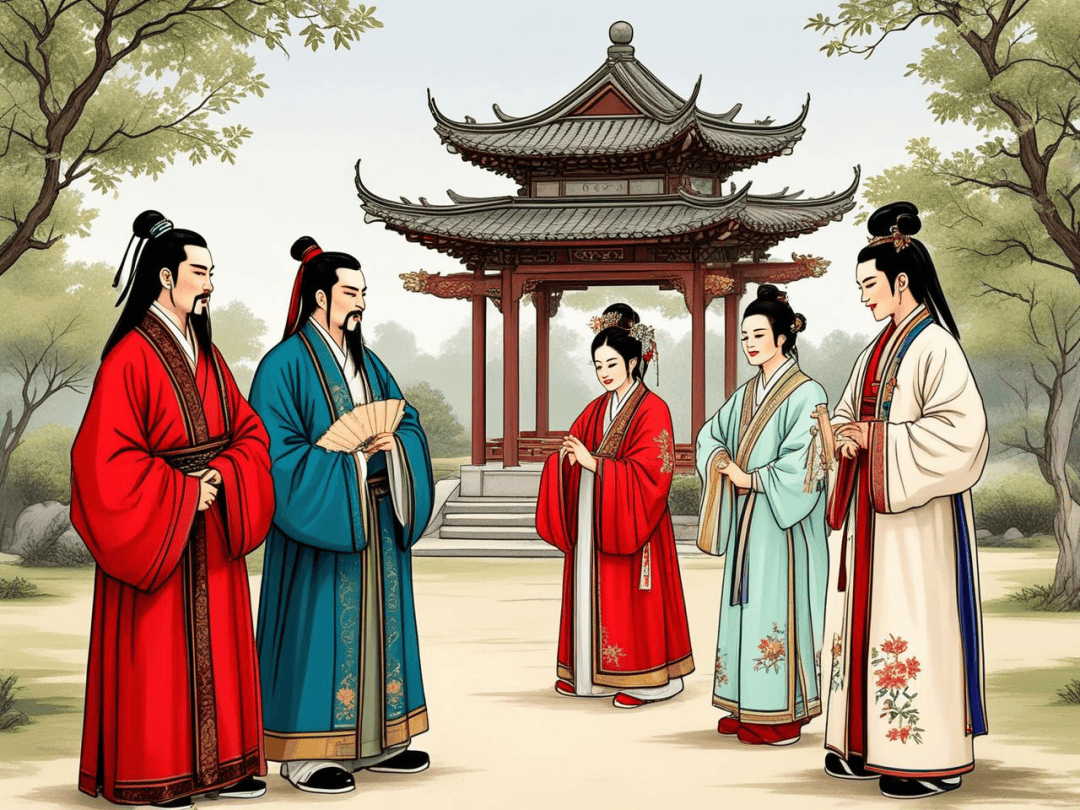
️二、时空交叠:庄园里的三重叙事
这座庄园的时空是折叠的。当暮鼓敲响三声,戏台上的杜丽娘褪去水袖,现实中的柳小姐便要换上洋装,去女子学堂教授英文。而当晨光初现,丫鬟小桃会提着竹篮穿过九曲回廊,篮中是给账房先生送去的参汤——这位从西洋归来的新派青年,总在油灯下算账至深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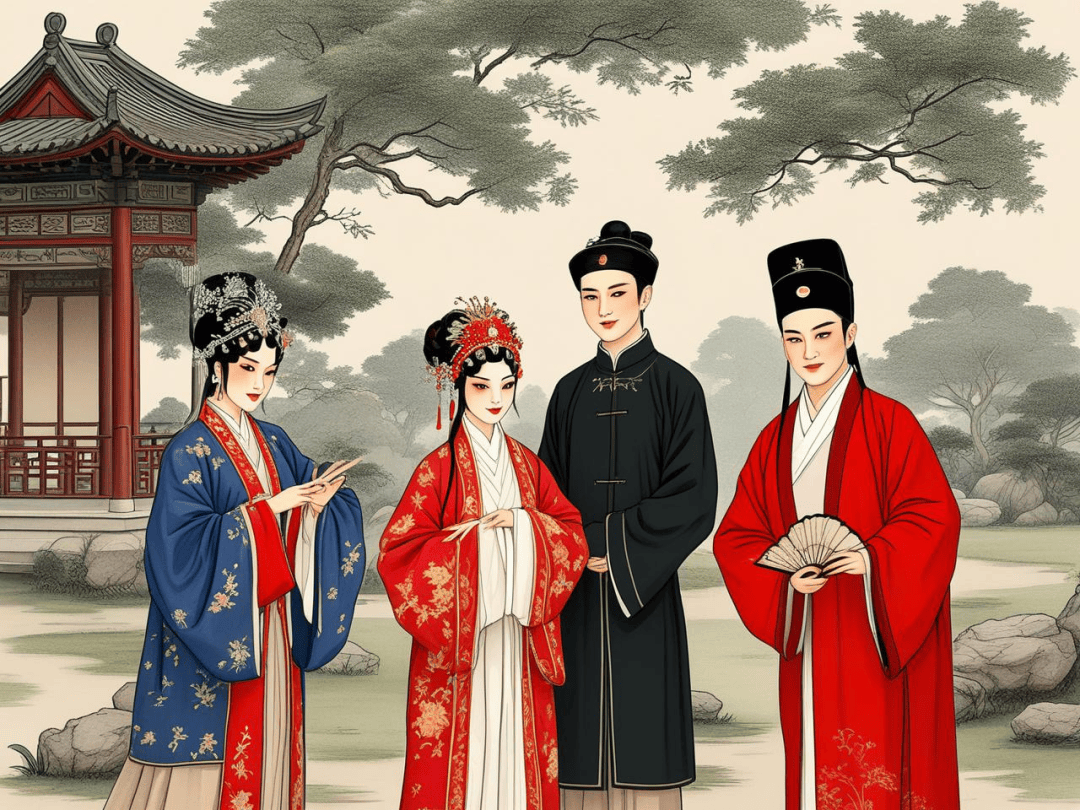
最耐人寻味的,是正厅悬挂的那幅《柳氏宗族图》。画中三代同堂的盛景里,藏着诸多隐喻:老太爷手中的茶盏是明代成化年间的斗彩,杯底却刻着“大清乾隆年制”;站在他身侧的二公子,面容竟与如今在戏台演柳梦梅的小生如出一辙;而最右侧那个执扇的模糊身影,据陈伯说,是三十年前离家出走的二小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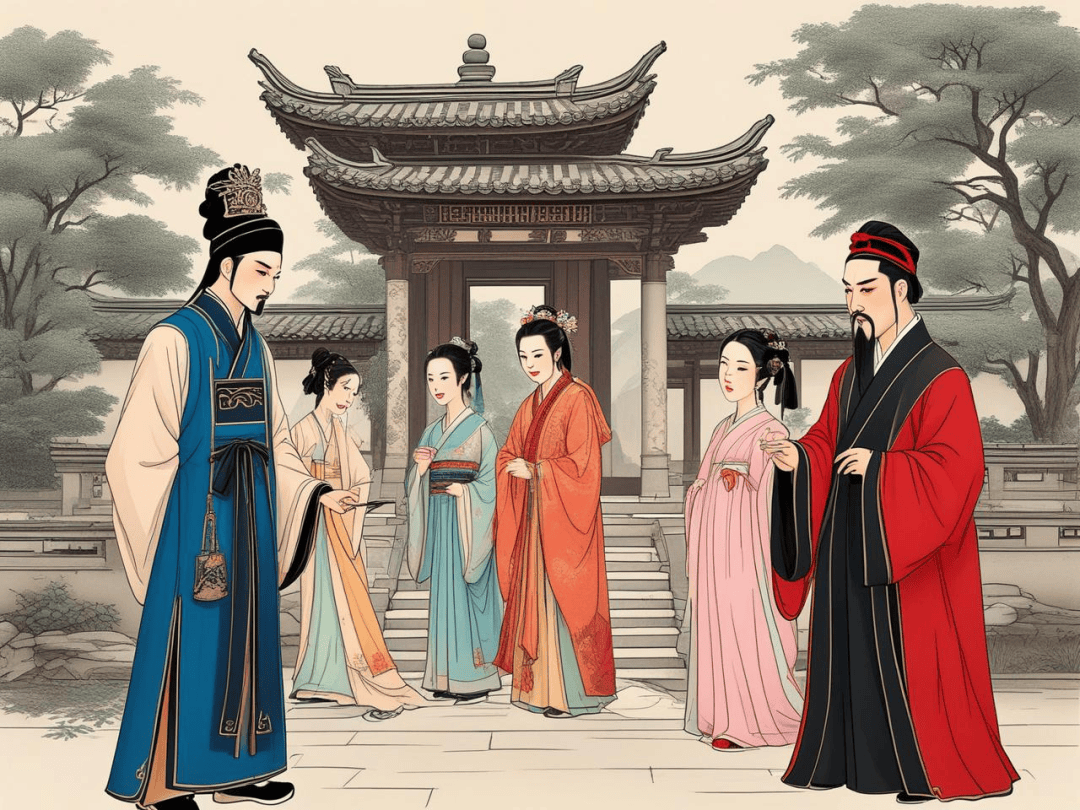
某日暴雨,戏班不得不停演。苏婉娘在后台卸妆时,发现妆奁底层压着半阙残词: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字迹娟秀却力透纸背,落款处朱砂印已模糊难辨。当夜,柳小姐房中的西洋座钟敲过十二下,苏婉娘看见她对着铜镜描眉,镜中倒影却渐渐幻化成戏台上的杜丽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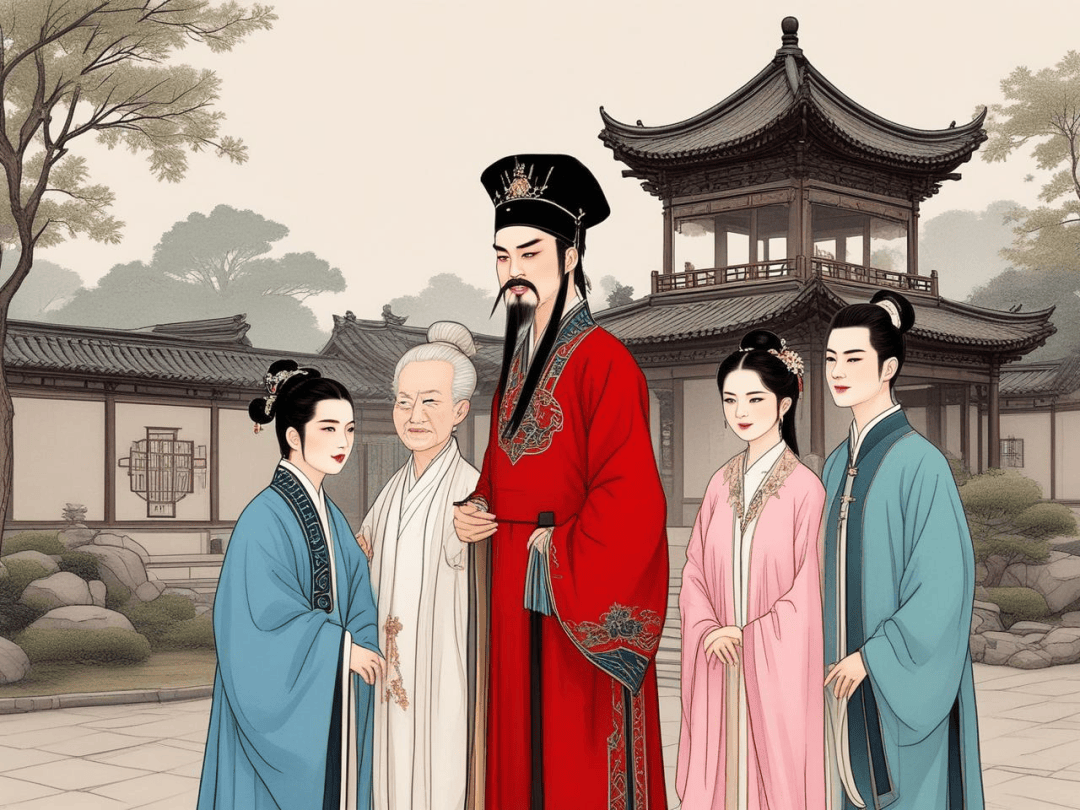
️三、戏曲内外:传统与现代的拉锯
账房先生陆明远是庄园里最“格格不入”的存在。这个留英归来的青年总爱穿着西装三件套,在账房里用钢笔记录收支,却会在每月朔望之日,默默往功德箱里投下银元——那是给戏班的月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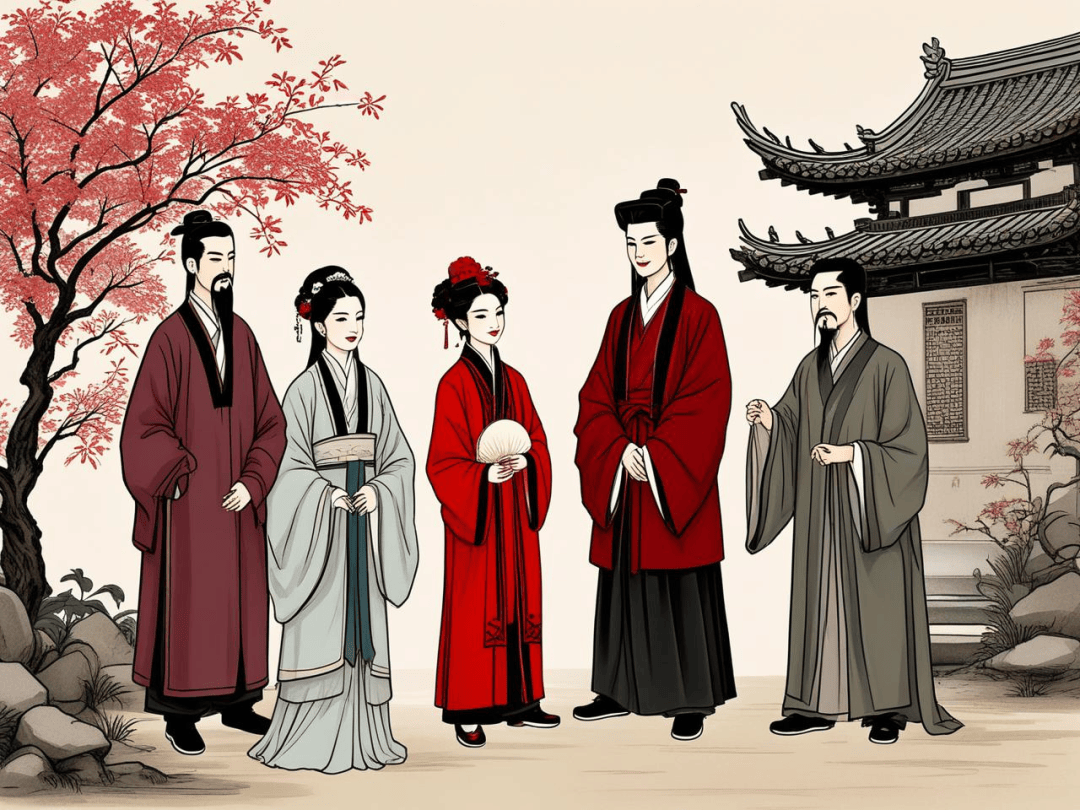
“戏曲是活着的文物。”陆明远曾对柳小姐说,“就像这座庄园,拆了梁柱改建洋楼容易,可要重建这满园的诗意却难。”他指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:“上月茶楼包场的收入,足够修缮三处漏雨的厢房。”
但变革的暗流仍在涌动。柳家少爷从上海请来的工程师,正拿着图纸丈量后花园:“这里可以建纺织车间,那边盖工人宿舍……”老周抱着祖传的《江南园林营造法式》冲过来理论,却被陈伯拦住:“让年轻人试试吧,就像当年老爷让我学用算盘替代算筹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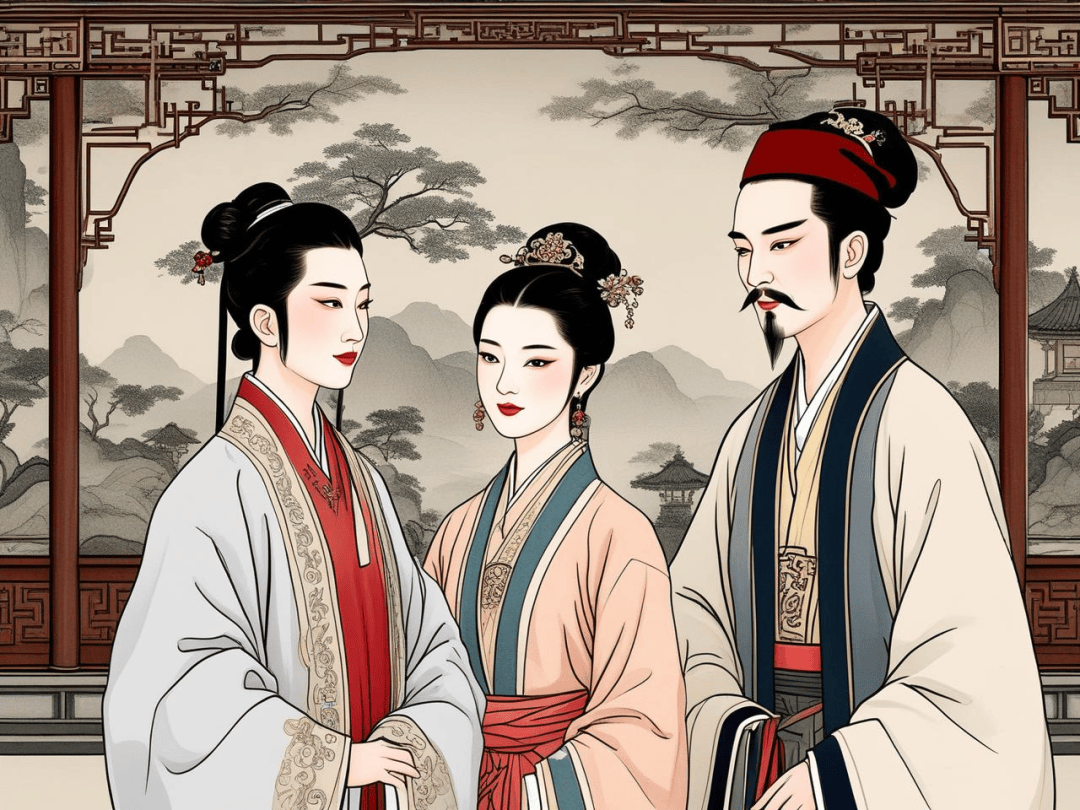
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中元节。按旧俗,这天要请戏班唱《目连救母》超度亡魂。陆明远却主张改放《义勇军进行曲》:“现在国难当头,该唱些振奋人心的。”两派人马在正厅僵持不下时,苏婉娘突然开口:“不如唱《牡丹亭》的《惊梦》折子戏,既有儿女情长,也有家国隐喻。”
这场争论最终以折中方案收场:戏班先唱《惊梦》,再奏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当“良辰美景奈何天”的唱腔与激昂的军乐声在庭院交织时,柳小姐忽然发现,父亲临终前塞给她的翡翠镯子,不知何时已戴在了苏婉娘腕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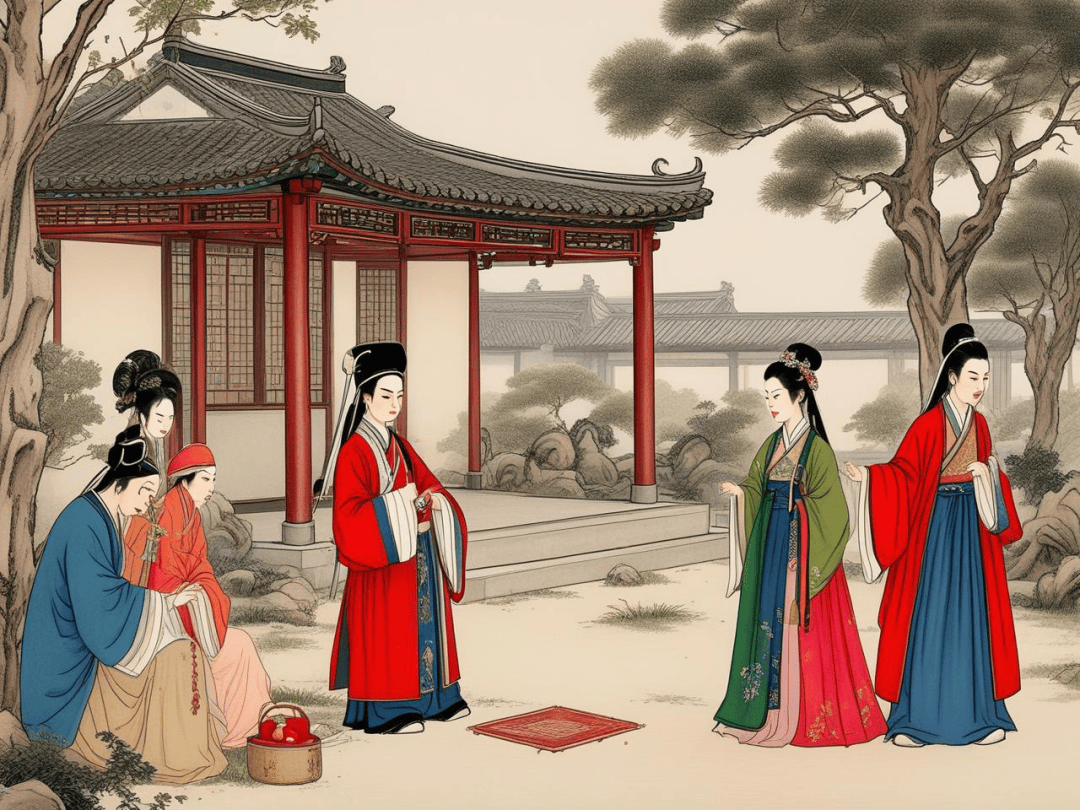
️四、暗潮涌动:那些未说出口的故事
庄园的地下密室里,藏着更多秘密。陈伯每月初七都会独自下到此处,擦拭那些蒙尘的戏服。其中一件孔雀蓝的靠旗戏服,衣襟处绣着极小的“婉”字——正是苏婉娘的名字。

小桃在整理小姐闺房时,意外发现个檀木匣。匣中除了泛黄的戏票,还有封未寄出的信:“……今日见你演《长生殿》,忽觉杨贵妃饮下金鸩酒时的眼神,与母亲临终前看我时一般无二……”信笺边缘晕着水痕,日期是民国二十三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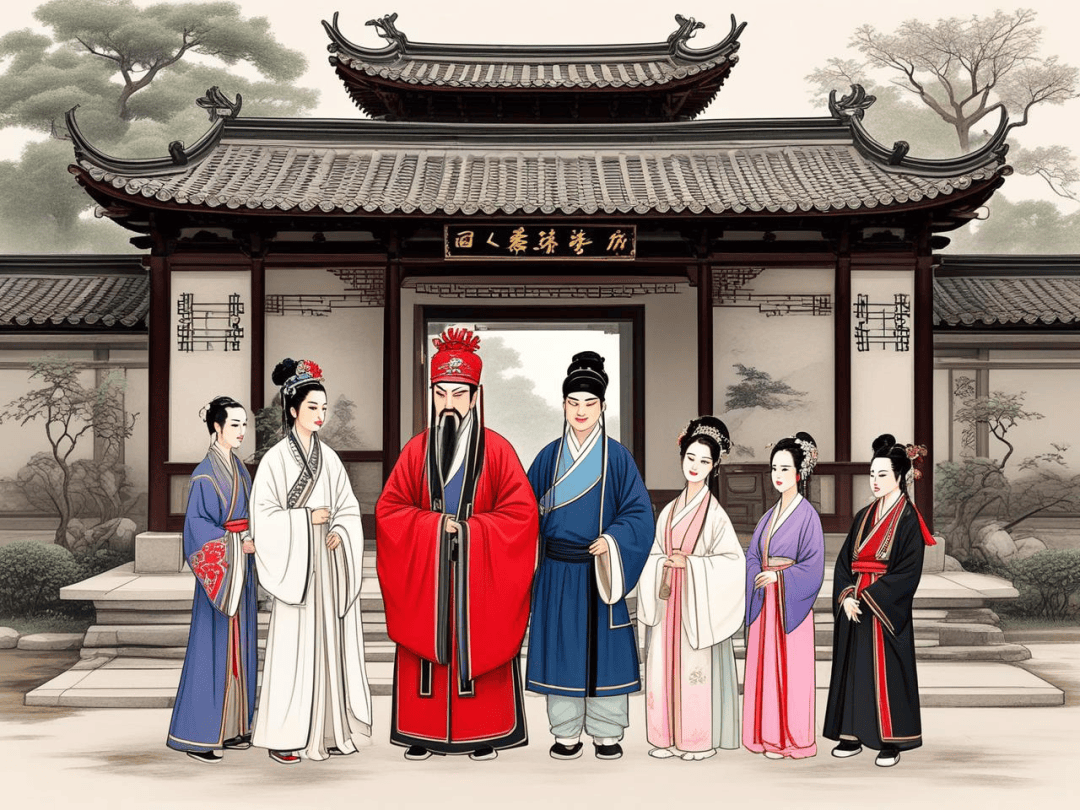
最令人心惊的,是账房暗格里那本《柳氏产业分布图》。泛黄的纸页上,密密麻麻标注着庄园名下的茶山、盐铺与当铺,而最新添的朱砂笔迹,赫然圈出了戏班驻扎的西跨院。

当这些线索逐渐拼凑完整时,某个雪夜,戏班突然不告而别。苏婉娘只留下支点翠簪子,簪头刻着极小的“柳”字。陈伯望着空荡荡的戏台,突然哼起《玉簪记》的唱段:“月明云淡露华浓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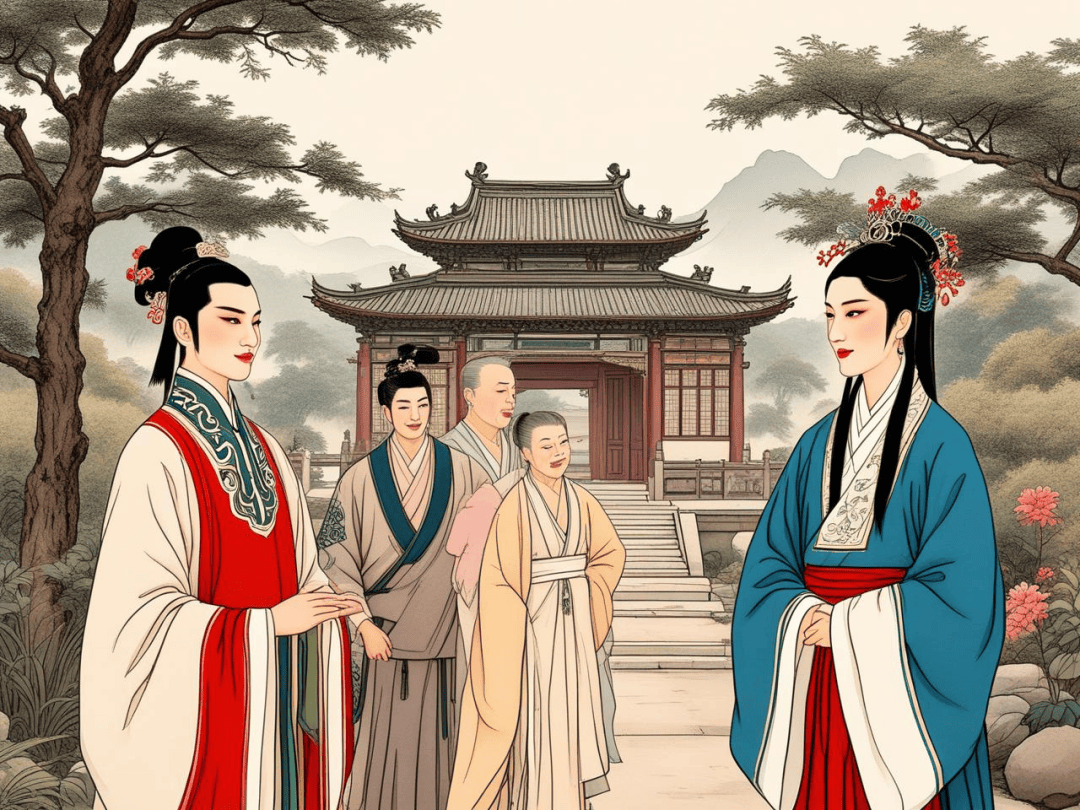
️五、余韵未绝:传统在当代的重生
如今,这座庄园已辟为戏曲博物馆。正厅的多媒体屏幕上,滚动播放着当年戏班演出的影像:苏婉娘的水袖扫过镜头时,恍惚可见柳小姐的侧脸;陆明远西装革履地站在账房,身后却传来《牡丹亭》的唱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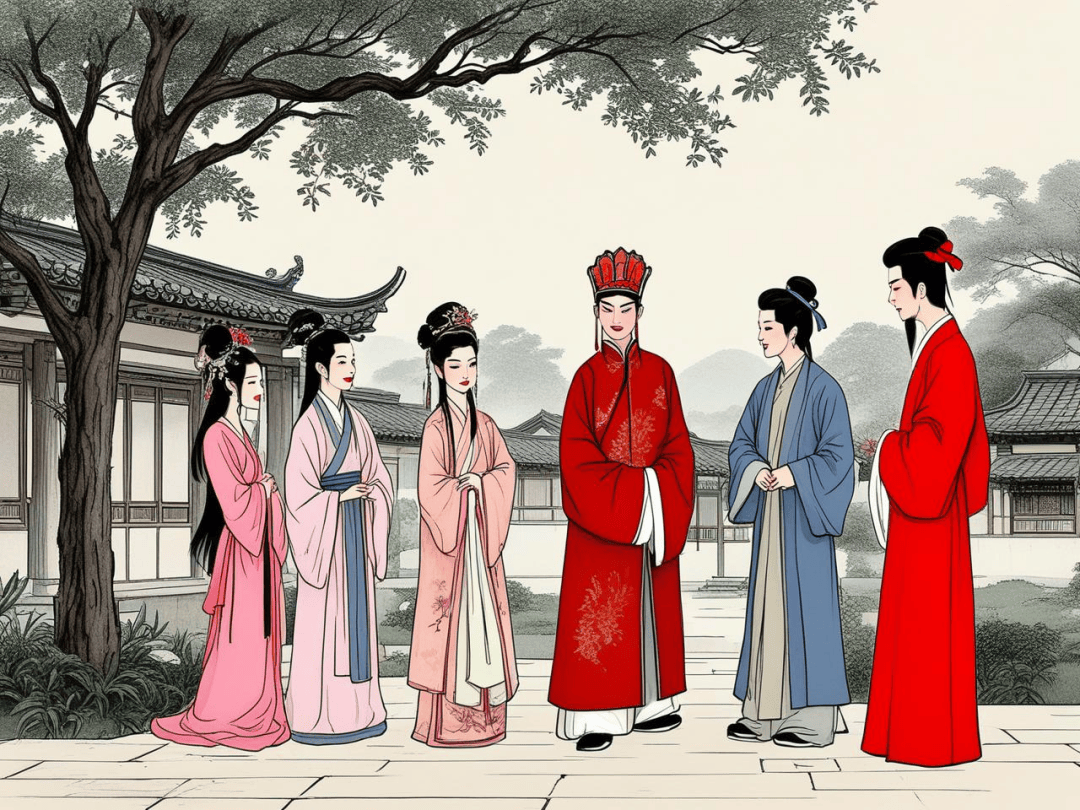
最受欢迎的展品是那件孔雀蓝戏服。当游客触摸感应装置,戏服便会亮起全息投影——五十年前的苏婉娘与五十年后的柳小姐,隔着时空对唱《游园惊梦》。而当年剑拔弩张的纺织工坊遗址上,建起了戏曲主题民宿,每个房间都以经典剧目命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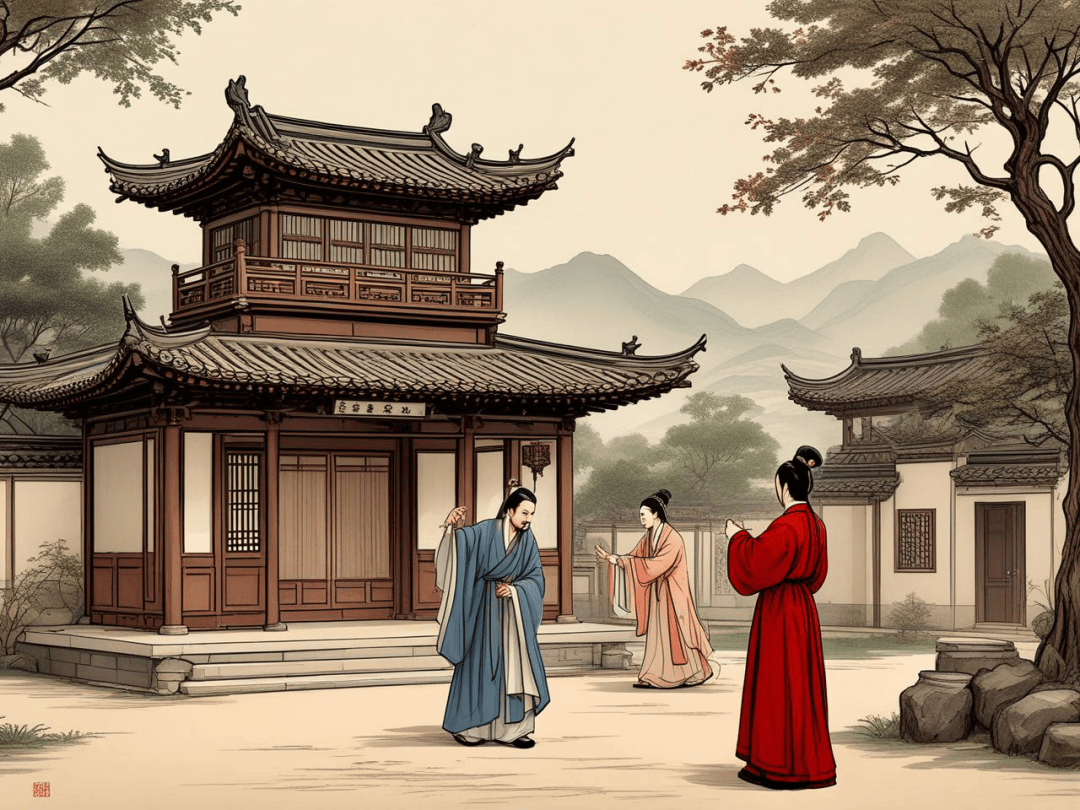
暮春时节,仍有游客听见若有若无的戏腔。老周的孙子如今是博物馆的讲解员,他总爱指着西跨院的梨树说:“这树是苏老板当年亲手栽的,如今每到清明,开的都是双色花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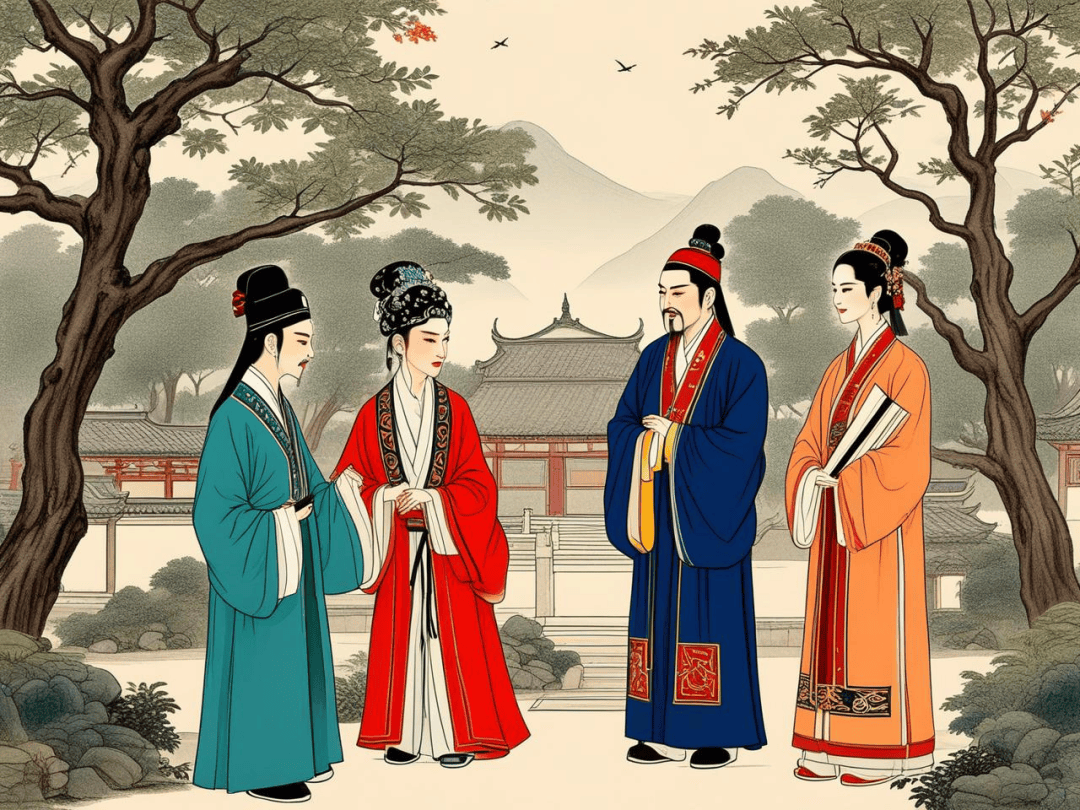
而陈伯的紫檀拐杖,如今静静躺在展柜里。拐杖头嵌着的翡翠,与苏婉娘留下的点翠簪子,在射灯下交相辉映。解说牌上写着:“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和解,是守护者与革新者的共舞。”

当最后一缕夕阳掠过飞檐上的嘲风兽,博物馆的智能系统自动播放起《牡丹亭·皂罗袍》。曲终时,不知何处飘来柳小姐最爱的栀子花香,恍惚间,又见那袭月白襦裙掠过回廊,衣袂翻飞如蝶。


